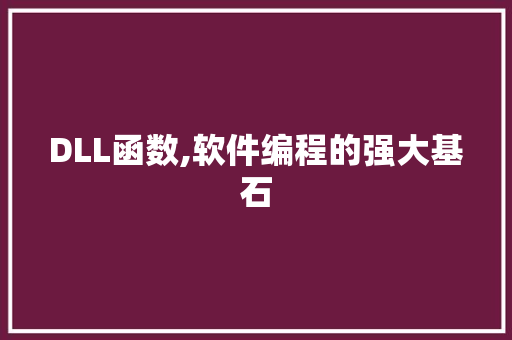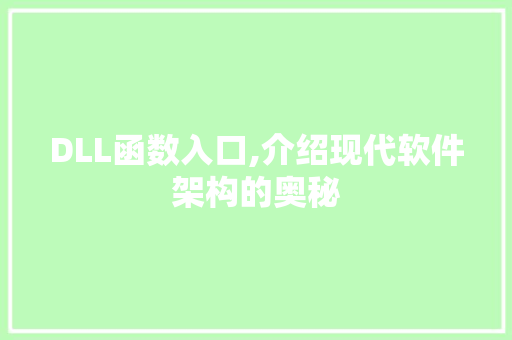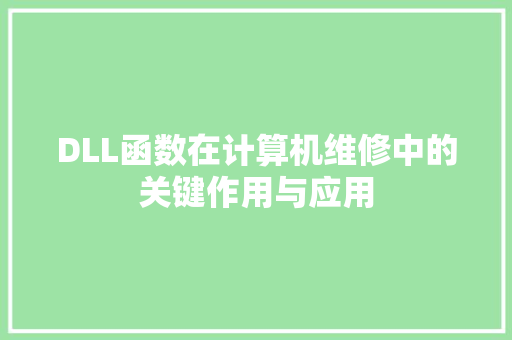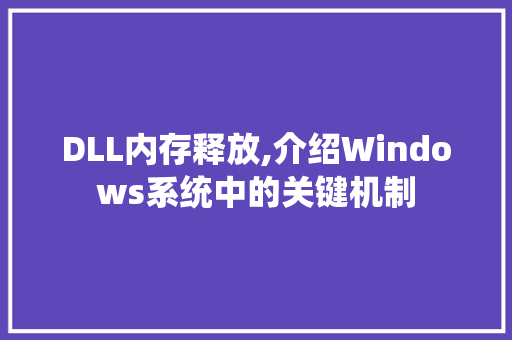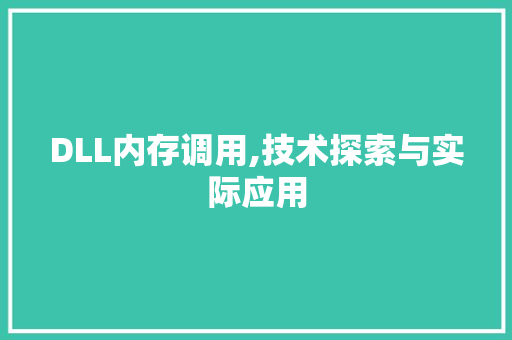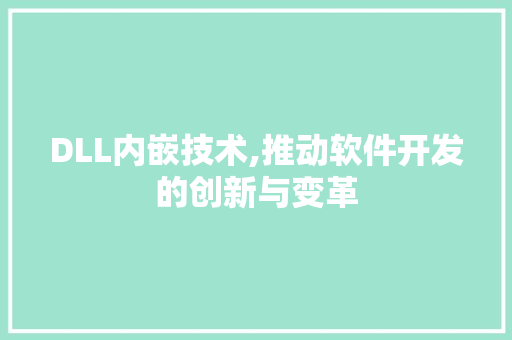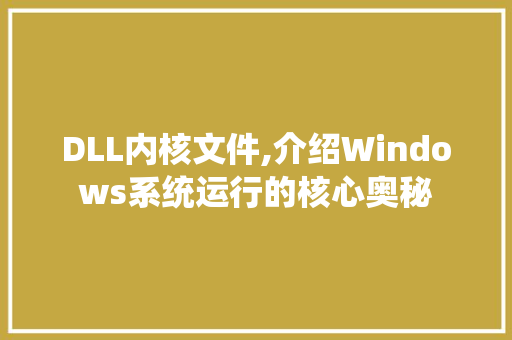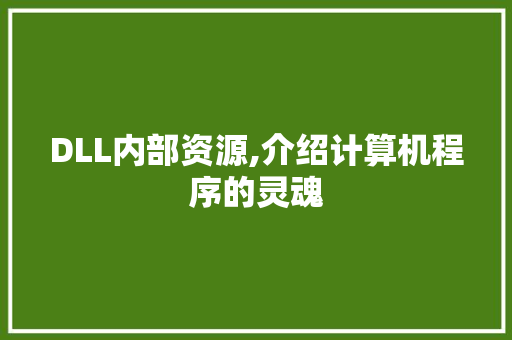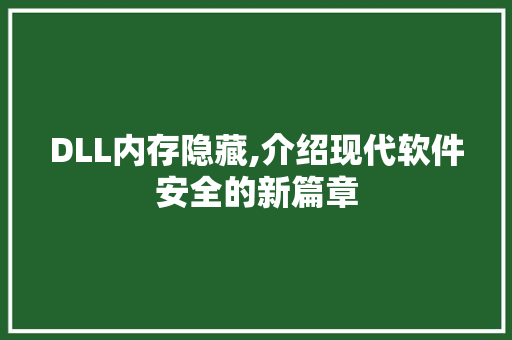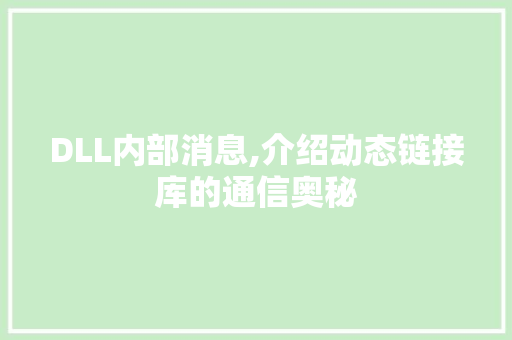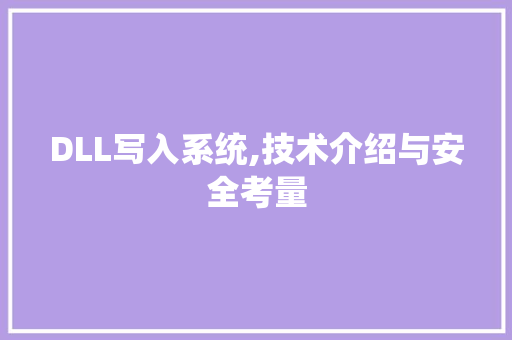上午10点,是罗先琼5年来固定的开工韶光。渝北逼仄的老街旁,上一坡石台阶,走过2米长的石栏走廊,用水泥砌成的小鱼池中,几百尾巴掌大小的鲫鱼拥挤地游窜着。罗先琼要做的,是用鱼篓子装上几斤,再用2、3公分长的水果刀把鱼剖开、洗濯,如果恰好鱼肚子里有鱼蛋,再重新将它们堪堪地塞回鱼肚子。
走廊前端,60岁的老伴冯家平身着海魂衫、头戴海军帽,斜靠在墙边,嘴边的喷鼻香烟已燃到尽头,他敦促几声,接过鱼篓,转身走进只能容下一人的厨房,下油、码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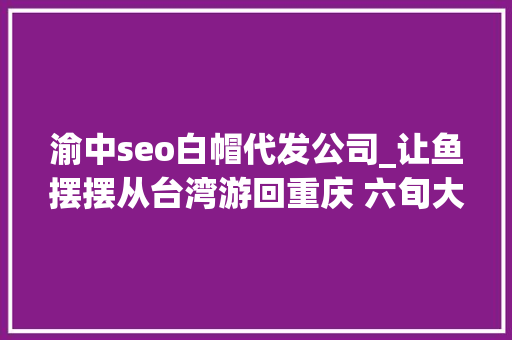
冯家平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大双此时恭候在侧,等着一锅油料鲜红的鲫鱼从父亲手里出锅。店里当天的第一桌客人已经落座,嚼着赠予的毛豆,等待着一快朵颐。韶光不到11点,午饭尚早,4人组成的吃货团队是一群熟客,见冯家平的小儿子小双在摆放桌椅,有一茬没一茬的和他聊起了家常……

冯家平的餐馆,是重庆最常见的家庭作坊。不知是直来直去的个性造就了重庆人的饮食习气,还是饮食习气影响了人们的个性。总之,重庆人对吃有独特的癖好:只要好吃,便不论味道之外的统统。换一种说法,重庆食客眼中,餐馆只有两种,好吃的与不好吃的。
冯家平的店,属于前者。
老街不宽敞,旁边两边停满了私家车,只留下一个收起后视镜才能驾车通过的狭窄空间。但这并不影响食客们用餐的“决心”。喷鼻香辣的土鲫鱼和啤酒,早已成了夏夜里老街人行道上的固定风景。
然而,即便是熟客,很多人也并不知道,冯家平的“鲫鱼”背后,有一个关于乡愁与亲情的故事。
冯家平
味道
持续暴雨,让今年的山城过了一个非范例的7月,直到8月开头,日头彷佛才变回了原来的样子。冯家平喜好这样的景象,越是闷热的傍晚,越有短袖、赤膊的食客在餐桌旁一边挥汗如雨,一边吃得过瘾。
味道鲜美的鲫鱼
他经营的是重庆最常见的“江湖”馆子,要说有什么不同,大概只有印刷在墙壁上,一张放大、复制的证件,上面用繁体字写着:
姓名:冯国钧
籍贯:四川省合江县
退伍时军阶:上士
……
这张证件的所有者,叫做冯国钧,是一名国民党退伍军人。“他是我父亲唯一的兄弟,我的幺爸。”厨房中,冯家平摆弄动手中的大勺阐明着。几勺油下锅,大火将锅子烧开,放进自家弄的泡海椒,少盐、少糖,乃至不用味精,下鱼、加水,一锅麻辣鲜喷鼻香的鲫鱼不久后便能出锅。
罗先琼在准备配菜
这样的烹饪方法,冯家平是从幺爸的手中学来。但冯家平自己也分不清楚,幺爸做的味道究竟是从何而来。如果说是幺爸从***带来的味道,泡海椒的底味,证明这应该属于地隧道道的川菜;但如果说这是四川的味道,却又不那么确切。
冯家平在从泡菜坛里抓出烹饪所需的泡海椒
上世纪40年代,幺爸曾是长江上的船工。那时,长江行船艰险,偶尔弄点新鲜的江河鱼,他就喜好用自己做的泡海椒,加一点姜蒜,用热油一过,做成麻辣鱼大饱口福。后来,他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之后又被带到***。这一手做鱼的手艺和方法,他在***给自己做了一辈子。直到回大陆寻亲,才将它带回了大陆。
搞不清楚地域的来历,但冯家平却分得明白韶光的差别。幺爸的鱼做了一辈子,乃至可以回溯到民国期间,1942年。于是,他有了店名。
冯家平在厨房烹饪鲫鱼
乡愁
在冯家平的影象中,1992年,重庆上刊登过一则***。***的标题是什么,文化不高的冯家平早已记不清。他只记得,报纸上彷佛是一张两位老人抱头痛哭的照片。一位是冯家平的父亲冯树云,另一位,则是幺爸冯国钧。
冯树云只有一个弟兄。上世纪40年代,冯国钧被抓壮丁带走,之后便再也没了音讯。
幺爸是怎么被抓走的,冯树云从来没有给子女提及过。但冯家平和兄弟姊妹们都记得,每年春节团年,父亲都会多摆一副碗筷。他说,那是幺爸的位置。
“幺爸是不是去世了?”冯家平曾这样问父亲,空碗、筷子,怎么看都像是纪念往生之人。但没想到父亲却发了脾气,冒了火。“正好是他以为,幺爸一定在世。只是这辈子可能无法再见。”
幸运的是,父亲去世前不久,幺爸回来了,还幸运地找到了他们一家。
幺爸冯国钧(戴白帽者)回重庆寻亲时与冯家平一家合影
1992年,冯国钧回到大陆。失落去联系40多年后,他并不认为,自己能成功寻亲。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了重庆市政府,供应了哥哥的名字,籍贯信息。
幸运的是,事情职员虽然在渝中区找到100多个冯树云,但籍贯合江的却只有1个。更巧合的是,当年卖力帮冯国钧查询的事情职员老王的儿子,正好是原重庆灯头厂的职工,冯家平是厂里的驾驶员。
“见面第一句话,幺爸问父亲,‘妈妈还在吗?’父亲说:‘去世很多年了’。之后,两位60多岁的老人便哭成了一团。”这是冯家平42岁那年第一次见到幺爸时的场景,想回家半辈子,幺爸没见着母亲,但总算是回来了。
冯国钧在***并没有子女,形单影只。便对哥哥的几个子女视如己出。1993年,冯家平的父亲冯树云去世,冯国钧依然和几个侄儿、侄女来往紧密,先后6次从***回渝探亲。
幺爸冯国钧(戴白帽者)回重庆寻亲时与冯家平一家合影
“大概是我当过兵,还在部队做了两年炊事员,以是和幺爸特殊投缘。”冯家平的影象中,幺爸并不常说自己的过去,但却特意教了他这道泡椒鲫鱼的做法。幺爸说,这道菜他自己做了半辈子,从大陆带到***,又从***带回大陆。
他还记得,幺爸曾给他念过那首著名的《乡愁》: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宅兆,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我没读过什么书,但这首诗我听得懂。幺爸的乡愁,也在他教我做的这道鱼里头。”
冯家平在厨房烹饪鲫鱼
遗产
1996年,幺爸溘然倒下了。这是他第六次从***回重庆探亲。那一天,他在家里溘然倒地,冯家平和家人将他送到了医院。冯国钧一贯想要说什么,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便匆匆离开了人间。
“他曾说,在***还有一笔遗产留给我们几姊妹,但末了,什么都没有说。”冯家平说,幺爸只留下了随身的衣物和几百美元现金,他们用这笔现金,给幺爸买了墓地,办了葬礼,好生地下葬,生活便又回到了***。
90年代末,冯家平所在的重庆灯头厂经营不善倒闭,他失落去了事情,但还好留下了开车的手艺。于是,他当了8年的公交司机,开当年的“康富来”中巴车。后来,他又做了8年的旅游大巴司机。而妻子罗先琼一贯没有正式事情,给人跑腿、打工,什么事情都做过。
2016年,渝中区的老屋子拆迁,老两口搬到了渝北居住。此时,冯家平附近退休,虽然大女儿已大学毕业有了自己的事情和生活,但双胞胎儿子,还须要老两口的帮补。
“我当过兵,什么难题我都不怕!
我做过炊事员,开个小餐馆没啥问题。”冯家平的想法大略而朴实,于是他和老伴商量,开一家鱼庄,就卖幺爸教他做的这种口味的鲫鱼,还取了个独特的名字——1942民国鱼庄。
冯家平将做好的鲫鱼端上桌
“在这地方来开餐馆,有买卖就怪了。”背街小巷,逼仄的店面。罗先琼说,店铺刚开张时买卖很差,乃至持续几天都没人光顾。过路者冷嘲的言语,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鱼做的好吃,我们对顾客激情亲切,买卖肯定会逐步好起来的。”老两口抱持着最朴素的理念,坚持着自己的一套逻辑,家常里短地和客人谈天,把所有客人当成朋友。
不知是冥冥中的运气,还是量变积累的质变。2017年,一位食客在用餐后十分满意,帮他们找来了重庆电视台干系栏目的,让鱼庄在美食节目上露了脸。这一次有时机遇,一下打响了这里的名头,前来的食客数量险些翻倍,鱼庄的买卖进入正轨。去年,抖音上的一个美食播主前来用餐后,主动帮老两口拍了抖音推广。第二天,鱼庄排起了长队,很多慕名而来的网友乃至排到晚上9点多,也没能吃上。
“小伙子,味道如何哟,有见地就提哈,我们好改进!
”晚上10点,又有一桌客人吃完买单,冯家平和平时一样,递上一支喷鼻香烟,很快和食客熟络地聊起了家常。罗先琼从厨房出来,也加入了“谈天团”,和客人开起了玩笑。
见罗先琼说话比自己麻利,冯家平退了出来,随手又递给一支烟。他咧嘴笑着说:“哪个说幺爸没给我们留下一分钱遗产,这便是他给我的遗产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