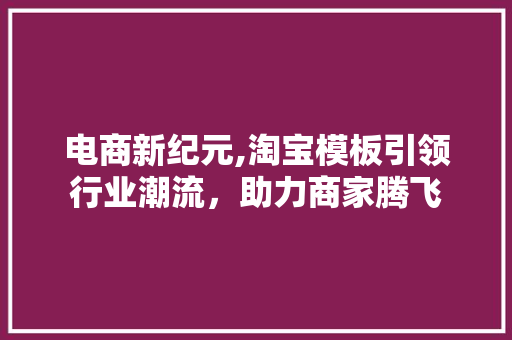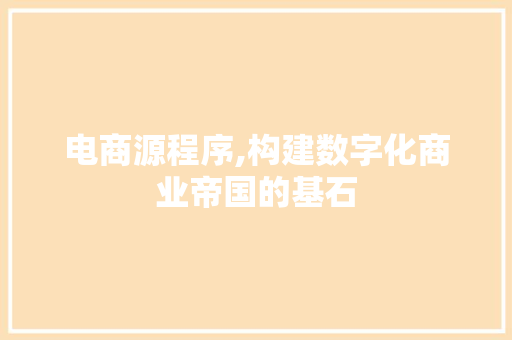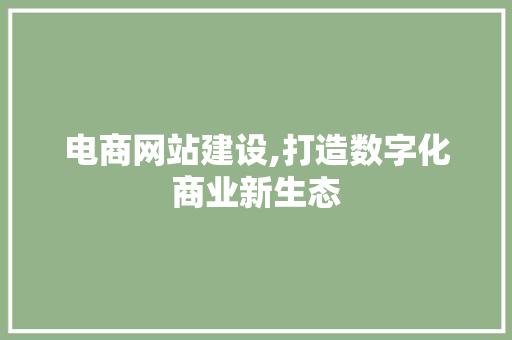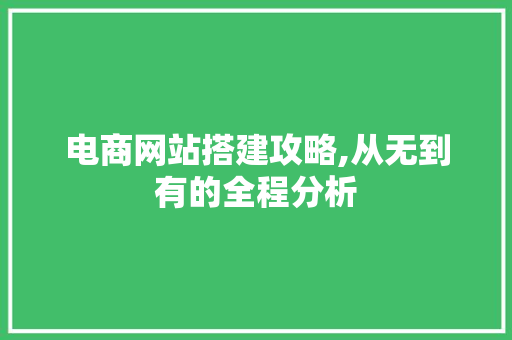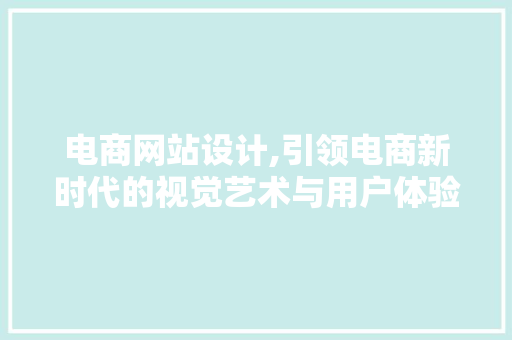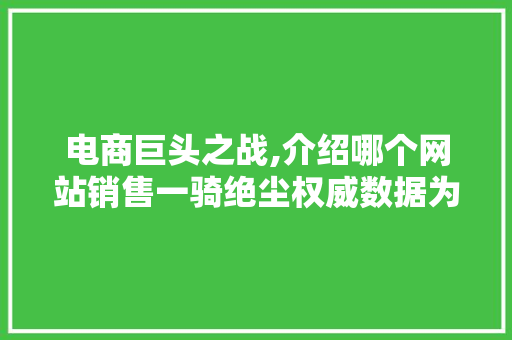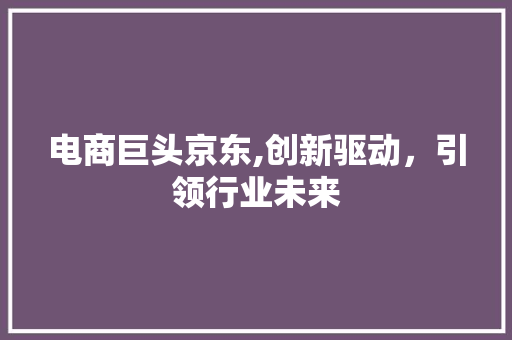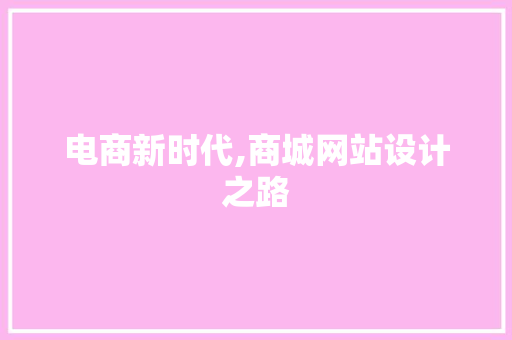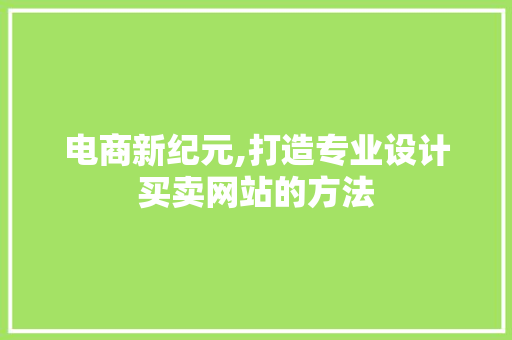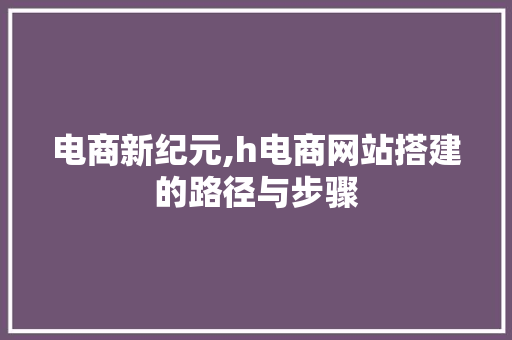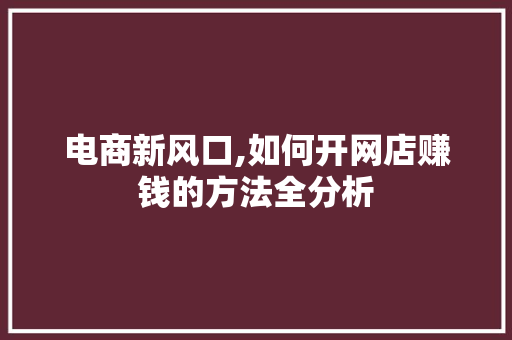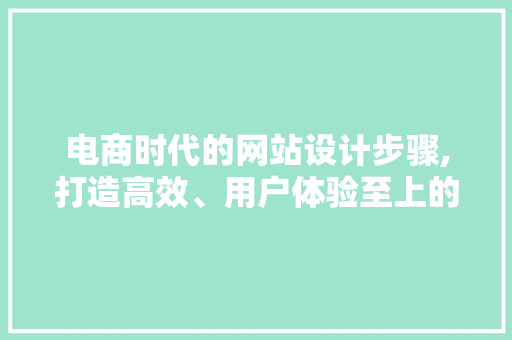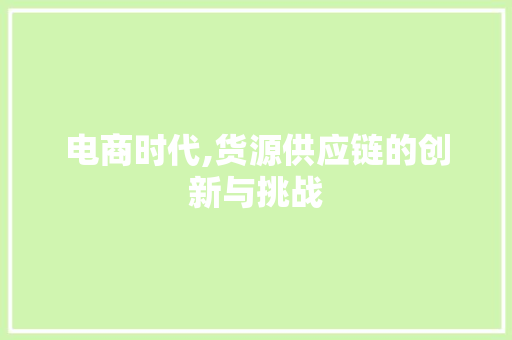与脉冲星有关的中国故事
“天眼”FAST调试与试不雅观测事情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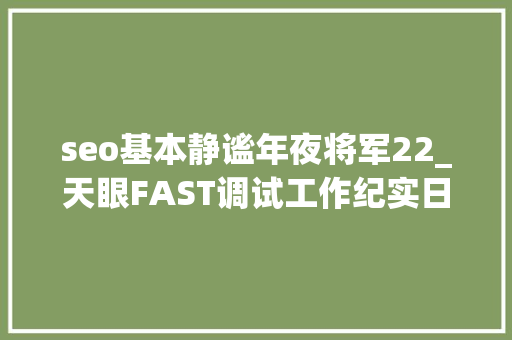
事情和想象的并不一样。

“本日晚上从9点55分开始不雅观测,持续到来日诰日早上8点30分。” 终于争取到进入FAST基地总掌握室体验望远镜不雅观测的机会,决定瞪大眼睛熬一整夜。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之上的星空。FAST拍照团队供应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刚宣告了一个喜讯——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首次创造毫秒脉冲星,再次引发了大家对天文的激情亲切,于是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前往贵州,揭秘创造脉冲星背后的故事。
但这个100平方米旁边的总掌握室太让人意外了——这里没有严阵以待穿着统一制服的事情职员,没有会变出奇异图形或繁芜代码同时还闪着各种不同颜色光的大屏幕,没有紧张的口令,没有急匆匆的脚步声,也没有击掌和欢呼声……只有一排电脑安静地端坐在桌子上,和一个同样安静地端坐在电脑前的年轻小伙子。
“你的同事还没来吗?”试探着问。
“他们输入完不雅观测数据已经走了。我一下子写完总结也走了。” 小伙子叫李志恒,操作条记本电脑,身穿白T恤衫和牛仔裤,是FAST调试组的一名工程师。
9点55分到了。从迢遥的太空传来的电磁波无声无息地落在群山环抱的大窝凼里,然后转换为旗子暗记安谧地流淌进打算机集群,打算机沉默地跑着数据,凭借调试职员设计的程序努力辨别脉冲星旗子暗记。
原来,那些震天动地的新创造出身得这么安静。
与脉冲星有关的中国故事,就从这个万籁俱寂的地方开始。
两位学者之辩论
古今中外,总有一些人想弄明白这几件事:我们从哪儿来?宇宙有多大?最小的粒子有多小?
在贵州的深山里,就有这么一群人。
写落成作总结的李志恒打开一款名为Stellarium的天象仿照软件,展示出一片效果逼真的太空。“我们的事情有点像淘金。” 他指着银河系的繁星对说。
目前环球经认证的脉冲星共有2600多颗,它们可以成为人们研究“最小粒子”的实验室、帮忙探索宇宙到底有没有边界等。这种能对人类认知宇宙产生巨大帮助的天体就像金子一样罕有和宝贵。
只是,在2016年FAST落成启用之前,这项为人类天文奇迹“淘金”的事情中国还没有成为主力。为此,FAST的总工程师南仁东生前说:“别人都有大射电望远镜,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20世纪90年代初,在国家天文台事情的南仁东最初将中国的大射电望远镜梦寄托在了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SKA身上。那是一项大型国际科研互助项目,其技能路线是将上千个反射面天线和100万个低频天线组成一个超过100万平方米的吸收区域,网络来自宇宙的电磁波旗子暗记。
当时在国际射电天文圈里有两张生动的中国面孔,一个是南仁东,另一个是他的师弟,后来成为FAST工程副经理的彭勃。他俩轮流飞往国外参加研讨,执着地想将SKA的培植引入中国,别人笑称彭勃是“SKA独立大队”、南仁东是“SKA独立支撑”。
但有天这两个互为支柱的人吵起来了。
这条路越往前走南仁东越以为走不通,他开始反对在中国建SKA。“把SKA弄过来,弄去世你我,都弄不成!
” 他跟彭勃说,南仁东的学术风格以“谨慎守旧”著称。
“先弄过来!
弄去世你我,还有后来人!
” 彭勃和南仁东恰好相反,他外号叫“彭大将军”,出了名的敢想敢说敢干。
而后经由多次辩论和多方论证,南仁东和彭勃的同门师兄,天文学家吴盛殷打算出,在中国培植一个约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最得当,既能超越已有设备,又现实可行。大家便统一想法,将SKA的梦想,嫁接到现如今的FAST身上。
于是一群对探索终极问题有热心的人开始创业。
为理解决望远镜的支撑问题,他们须要找到一个天然的“大坑”,让望远镜像一口锅一样“坐”在里面;为理解决电磁波旗子暗记吸收机,即馈源舱的移动问题,他们须要设计一个可靠又省钱的机器构造;为了让望远镜能够在最大范围内灵巧追踪天上的目标,他们须要望远镜反射面能动——正是这些寻衅,逼出了FAST的三大技能创新。
梦想裹挟着创新的风险一步一步把韶光的坐标推到本日。他们成功了,FAST成为天下上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不过FAST工程团队名单上前三位中,南仁东和吴盛殷已去世,当年算得上是年轻人的彭勃也戴上了老花镜。
彭勃记得他从前作为留学生代表接管德国电视节目采访时说:“中国也要在望远镜灵敏度发展曲线坐标图里点个点!
” 朋友听了这话私下跟他说:“你敢在德国吹牛。要点个点,就必须做第一,当天下老大。”
“当老大就当老大!
” 他回答说。从FAST的想法成形,到本日成为环球最灵敏的宇宙“淘金”设备,过去了20年,只管韶光长了些,但彭勃并没有吹牛。
“那个造望远镜的过程就像有身。” 准备收工的李志恒见告,他转头看了一眼总控室的监测屏幕,接着说:“我们现在调试的过程,相称于要把这个孩子养育成才。”
韶光来到2018年,更年轻的人们连续探寻终极问题的答案。
无先例可循
FAST调试组正式成立于2017年4月,成员数10人,80后岳友岭是调试组的卖力人之一。调试组成员大多是FAST团队中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人,也是现在的中坚力量。
当年FAST令人骄傲的三项自主创新延伸至今,便意味着调试事情在国际上“无先例可循”。这些均匀年事30多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合法心翼翼地为射电天文不雅观测开辟一种新的、中国的办理方案。
“大略来说,FAST相称于人类感官的延伸。”总控室里的打算机集群嗡嗡作响,晚上11点多,李志恒连续搜肠刮肚地打比方。
我们的感官无法识别和处理宇宙中的天体传来的电磁波旗子暗记,FAST的运行系统就充当了媒介的角色,它将旗子暗记网络、处理、再翻译成人类能理解的形式。
但中间这个转换的过程非常繁芜。拿不雅观测脉冲星来说,天体呈周期性发射的微弱的电磁波射向地球,有一部分落在FAST的反射面上,反射面将这种电旗子暗记汇聚到馈源舱吸收机处,吸收机将电旗子暗记转换成光旗子暗记,通过光缆将光旗子暗记传回总控室,再把光旗子暗记转换回电旗子暗记,进而转换成数字旗子暗记,打算机集群就根据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将这些数字旗子暗记储存、打算,终极结合科学家的剖析,识别出能够代表脉冲星的一串分外的信息。
由于FAST的技能路线新颖,以上每两个逗号之间,都有难以计数的问题等着调试职员去办理。
岳友岭见告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截至去年年底,望远镜的功能性调试任务都已经完成,此后一贯在调试性能。望远镜性能的提升,便是精度的提高。”
以是他们现在的日常事情这天间“抠精度”,晚上试不雅观测。
远看FAST就像一口直径500米的大锅,“锅沿儿”上伫立着6个百米高塔,每个塔伸出一条钢索,6根钢索提着一个形状不规则的白色舱室移动,舱室的下方是由4450块三角形面板拼成的“锅面”,而“锅底”还有数千根钢索织成的索网,用来支撑这口“大锅”和牵引“锅面”运动。
让这个弘大的装置达到豪米级精度殊为不易。“抠精度”的过程,可谓险、难、繁、重。大家常常卡在某个问题上,“一卡便是一两个月”。
例如,FAST主动反射面的面板与面板之间有2225个节点,柔性钢索拉动节点位置运动以带动面板运动,形身分歧的抛物面,以达到反射面能够“跟踪”的效果。每根钢索靠插在大窝凼草丛中的液压杆匆匆动器驱动。工程师张志伟就管理着这2225个匆匆动器。调试以来,“通信延迟”、下雨、大雾、鼠蚁作乱等状况频频发生,为了让反射面面板“听话”,张志伟他们在一年多的韶光里设计出了上千套参数,以应对各种反射面变形需求。现在反射面节点的理论位置和实际位置偏差被掌握在了5毫米以内。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反射面上的丈量靶标。FAST拍照团队供应
再如,在精度达标的情形下,FAST采集到的数据就成了科学家可靠的剖析资料,他们和他们设计的算法一起,在海量数据里搜索脉冲星的身影。但难就难在,只管众人已知脉冲星可以发出周期性旗子暗记,可并不知道这个周期到底是多少,“可能是0.01秒、0.011秒、0.1秒……” 岳友岭说,因此科学家们须要一直地改进算法,去排查各种可能的周期,事情量其实不小。
岳友岭认为,FAST调试进度很难量化,只管试不雅观测效果已经超越了现有的其他射电望远镜,但要达到“好用”,还要办理数不清的问题。
“我们不怕折磨,我们能找出问题出在哪儿,便是须要想办法办理。”调试中碰着的“麻烦”在岳友岭眼里,都可以用“有趣”来形容。
岳友岭是个爱动手的天文专业博士后,38岁就头发花白,但仍有一双18岁的眼睛,里面写着空想和激情。他不以为自己苦,“立下汗马功劳的是那些年轻人”。
我们也挺伟大的
在调试事情中,岳友岭的角色是站在望远镜硬件调试和搜索脉冲星算法的衔接处,卖力确保旗子暗记准确无误地从望远镜流入到算法中。
现在岳友岭隔三岔五从北京跑一次贵州,打扮得像个风尘仆仆的背包客。他就属于那种乐于追求人类终极问题的人。
他可以耐着性子从FAST讲到脉冲星讲到引力波再讲到黑洞,绕一圈再讲回FAST,连续讲两个小时,只是一谈到自己就支吾不清。你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喜好留在FAST勤学不辍地办理各种“麻烦”,他只能拍着大腿幸福地重复三遍:“我以为这个事情特殊故意思……便是特殊有趣!
便是……便是……便是你小时候学过的那些事,现在终于可以自己亲手做了!
”
南仁东和彭勃把自己的人生倾注在FAST上20年,岳友岭和张志伟他们也已经干了快10年,在这些“牛人”面前,李志恒以为自己就像“小蚂蚁”一样微不足道。但他在这项全球瞩目的大工程里,也找到了自己的代价感。
和李志恒在总控室里的发言一贯进行到夜里12点,话题从“谈技能”转移到“谈人生”和“谈空想”。
“为什么说自己像蚂蚁?” 问。
“我们做的实在都是很小、很基本的事情。” FAST团队里像李志恒一样做根本事情的人很多,他以为:“大家就像蚂蚁搬家一样,举起块石头都不知道是谁出的力,但少了谁也弗成。”
趁着喘气的空当,他把写好的事情总结放在邮件里发给了上级。
“创造脉冲星的时候你愉快吗?” 问。
“愉快?是遗憾吧!
” 这是他的第一反应。
“我们探测到第一颗脉冲星候选体时没有急速跟南老师说,等到被认证了才见告他,发出的那封邮件他再也没回过。” 李志恒说,“南老师知道这个孩子会走了,会跑了,但没亲眼看到他拿奖。”
2017年10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宣告FAST取得首批成果——其探测到的脉冲星候选体中有6颗已通过国际认证,这是中国射电望远镜首次新创造脉冲星。而南仁东逝世于9月15日。
“不过,也还是会高兴。” 李志恒又想了想说。
宇宙之浩瀚弗成思议。可不雅观测的宇宙中含有1000亿个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而人类所在的银河系中含有1000亿个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可想而知,这些天体发出的电磁波穿越迢遥的时空传到地球上时已十分微弱。射电天文奇迹从上世纪60年代发展至今,吸收到的电磁波都加在一起转换成热量,也烧不热一杯咖啡。
李志恒以为,只管人类的感官没办法直接感知宇宙中如此微弱的旗子暗记,“却能凭着自己的一小坨脑花”,想出各种办法去探知宇宙里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想想,我们也挺伟大的”!
第二天下午,李志恒所说的“蚂蚁”工程师陆续聚到总控室,做当天的不雅观测准备事情,连续以“蚂蚁搬家”的办法,为射电天文科学的发展探索中国办理方案。
目前,FAST创造的脉冲星已超过15颗,接下来,它将从脉冲星“专业户”转型成多栖“不雅观天利器”。
最近,“天眼”将“眼珠”升级,安装了新的馈源——目前天下上唯一一台十九波束吸收机。这个新装备与原来的单波束吸收机比较,不仅可以将FAST的巡天效率提高数倍,还能够实现多科学目标同时不雅观测。
这意味着,未来不仅在脉冲星,而且在中性氢等天文不雅观测成果中,会产生更多的中国故事。( 张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