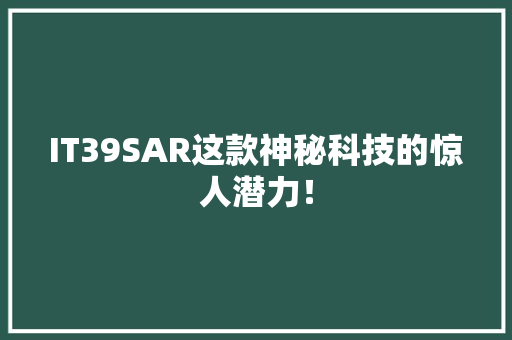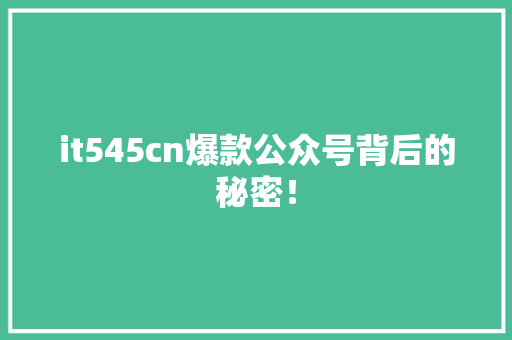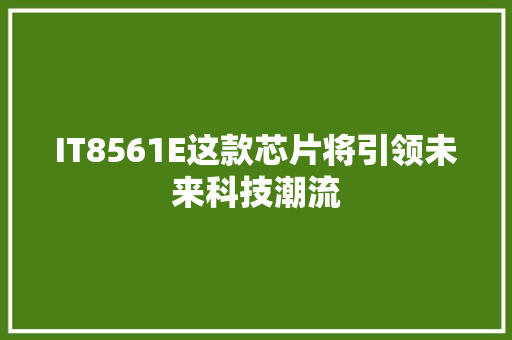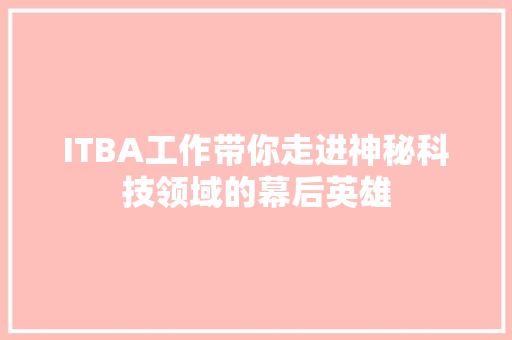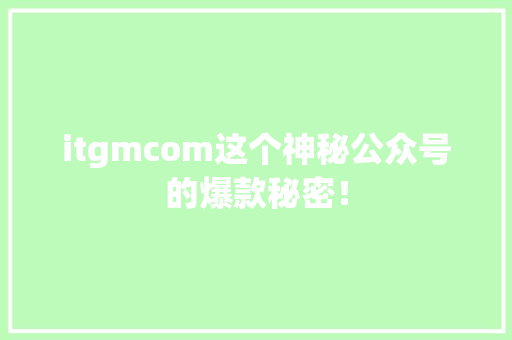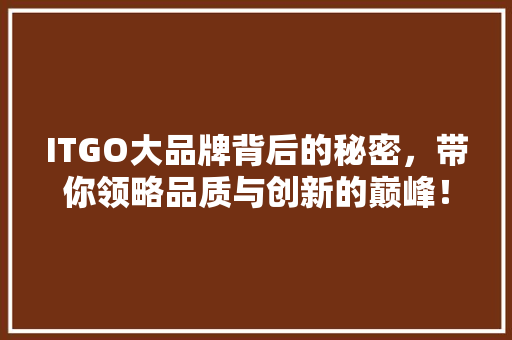在这个名为“日照”的滨海城市,阳光、沙滩、海浪、涛声,总是会让人想到漫长——漫长的时日,那么多的过往。海岸线在潮水的拍打中不断地向前延伸,一贯到看不见的远方。漫长,会让我们想到许多事物,比如悠扬而辽远的长调、连属无端一笔尽兴的草书线条、无从拂开的袅袅情思,还有那些难以言宣的期待。《大明宫词》里,太平公主请明清远给她看掌中纹路的走向,明清远说:“公主掌中纹路如凤尾悠长婉转,再看公主凤颜龙颈,真乃伏羲之相。”这就调动了不雅观众的想象——伸展的、蜿蜒的、细腻的、润泽的。
万平口从南到北展开的海岸线,使热爱徒步的人,故意施展自己的力量。这种原始的行走,要多久才能走到尽头?行走是人对大地的一种触摸,比安坐车立时更为真切。起先的一段时日,我曾赤足而行,如此,与地面有一种实在的摩擦,能感想熏染地面的平缓与波折,干燥与湿润。此刻,有人提着鞋子,在周详的沙子上走动。潮来潮去,沙滩清洁,双足在上,优柔如绵。此时是暮春,离旅游旺季还早,滋润津润中有一丁点凉意。人迹无多,会生起空旷岑寂的心思。海水盈满,不息地发出低沉的声响,从深处浮到海面上。细细谛听,涛声与涛声还是有差别的。我从东海来到黄海,对陌生之地生出了许多敏感和好奇,会将它和自己已经认识的场景比较——海水拂面的刚柔、海水起伏的强弱,还有海岸线不同的弧度。当年读曹孟德的《不雅观沧海》,以为他有些迫切了,他想把澎湃的情调塞入这短短的诗行里。现在我们沿海岸线行走,更多的是散漫、徐缓。人和自然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大海、沙滩、海岸线,千万年后还是如此,而行于海边的早已是另一些人。

插图:周艺珣

欧阳修曾说自己中年之前有许多艺文方面的爱好,后来都放弃了,只有写字被他保留下来。他认为写字可以“消日”。写字,给了人独立而为的机会——在书写中,自由、闲雅地任时日悄然滑过。许多文士喜于独自游历,独自书写,不管来日很多还是无多。欧阳修不在宋代大书家之列,但他的“消日”不雅观还是给人很多启迪——在徐缓中也能产生力度。人不是夸父,不必与日逐走而渴饮河、渭。太阳究竟是追不上的,反而让自己干瘪。如果认同“消日”之说,心绪天经地义沉着下来,眼神看世相多了一缕深婉不迫,笔下也能够生出轻逸之迹,此时可以称“松弛”了。一些人在不雅观光车上沿海岸线奔跑,一些人却不吝脚力,沿海岸线行走——前行速率不同,使得他们过后对海岸线进行的评说,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到万平口看日出,是许多行者的欲望之一。只管人们在故乡、异域已经看过不少日出——山岭中的、乡野间的、平原上的,但是来到适宜不雅观日出的地方,还是会早早起身,疾行至最佳的不雅观赏点。“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这句话已经没什么新意了,却还是能勉励人,让人悄悄等待。清晨的海边空气清新,昨夜的涛澜涌动,已经转为轻轻拍岸。远处水汽迷蒙,每一个缝隙都让潮气充满着,只等着红日初升时一举廓清。等待使人浮想,未露面的朝阳此时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没有谁能说清。它被一方厚重的樊篱阻隔了,光焰未曾泄露。天色逐渐明朗起来,有鸟群拍翅掠过,韶光又近一些了。爱看日出的人,心思或许是向上的、腾跃的、发达的,他们及时赶到,就为了不负朝阳冲出地平线的一瞬。互不相识的人们,只因爱好相同,自觉地聚拢在一起。
万平口也是看日落上好的方位。看日出和看日落的常日是两拨人,心境不同,意见意义有别。看日出可以感想熏染一种激情,相互分享喜悦;看日落则静默无声,彷佛无甚可说,自己有所感即可。午后的光阴很是温暖,心弦逐渐松动起来。夕阳开始西颓,全然可以把握它的行踪,也就不必迫切。看日落的人多数不是专程来的,他们恰好在海岸线上行走,或者在沙滩上休憩,遇上了,就顺便看看,全然不费心力、脚力。看日出是有变数的,总会听说某人到了哪座名山未能如愿看到日出的惋惜,逢雨逢雾,缘由不少,由此引发人们对无常的思考。而能否看到日落,大抵可以预见,这也使行者感到安逸,或坐着,或倚栏,随意的,遣兴的,看日头逐渐消逝,然后离开。日出有如一幕大戏开场,帷幕伸开时,统统都才开始,让民气怀残酷,犹豫满志。而日落则不同,虽然徐缓,究竟是逐渐向下行走。海边,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者由家人推着,彷佛在注目日落的轨迹,又彷佛视而不见。他更陶醉的彷佛是拂过面庞的那一缕缕风,这使他舒适之至。面对落日,最好什么都不想,只是纯挚地欣赏,如此就大略轻松了许多,任暮色逐渐合拢过来。
后来,我们乘船,到海的另一边。人与巨大的船比较,自见微小;而船比之于海,则又微小之至。人不是飞鸟,无从掠过大海的浩渺,但人高于飞鸟的地方表现在长于制造工具。工具制成了,或腾空而起,或破浪前行,抵达辽阔与迢遥。对付凡人来说,海上光阴只是人生的一点过渡,没有谁会在海上勾留太久。这也使写陆地的人多,写大海的人少,没有谁像琢磨陆地那般地琢磨大海。在船这个浮荡的空间里,若论提及大海的深度、广度,真是苍白之至。记得《晋书·王羲之传》中说:“与羽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去世。’”想当年王羲之陆上风光穷尽,浮槎泛海,感叹无限——一个人临海,会生出许多不同的思绪,哀乐、去世生、有无。在海上,也可以窥见一个人的襟怀、风姿。《世说新语》里写绅士谢安和几位朋友于海上泛舟嬉戏,不料风浪骤起,众人神采慌乱。船越前行,风浪越大,众人惊惧乱作一团。与之形成比拟的是谢安,他安坐船中视若等闲。后人以此不雅观之,以为谢安“足以镇安朝野”。
海边有一座森林公园。正是海洋的吞吐、舒卷、开合,使树种有了更多竞争。这里树种繁多,可知的有刺槐、黑松、杨树、水杉、雪松,更有浩瀚未知的。南朝梁的吴均曾这般描写:“负势竞上,相互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我不知吴均描写的是哪一种树,但在这个森林公园里,以此来描写水杉,再恰当不过。水杉这栽种物是有象征性的,正派、上行,有凌云摩景象象。一大片的水杉,给人的便是张放的气势,在半空中迸发出清洁的绿意。面前这片巨大的森林,像一张绿色的大网,在高处延伸。个中的细节极有条理——每一株树本能地方案着,使每一枚叶片都有和阳光雨露碰触的机会。生存的聪慧是千万年来逐渐积蓄起来的,不如此就要走向衰落和消逝。春日和煦、潮润,生者察觉到大自然的眷顾,一些新叶长出来了,一些枯枝掉落了。一些枝叶与母体紧密结合的同时,一些枝叶正分开母体,再无关联。统统了无声息,合于生存便是天道,不必伪饰、雕琢。我认识不少能写一手锦绣文章的文士,写作功夫已经娴熟之至,如珠走盘,然而若要言说欠缺,或许是笔意达不到闲云出岫、归鸟入林那般自然——信手、信笔少了,故意为之多了。钱谦益说得好:“天之生物也,松自然直,棘自然曲,鹤不浴而白,乌不黔而黑。”对付写作者来说,或许不是指腕间的问题,而是其他——随着年齿的增长,将名利看淡,不徇人矜己,笔下之痕有可能逐渐近于自然,犹如这里的一株水杉。
一个城市以“日照”为名,大抵缘于与阳光的亲密。在阳光的照耀下,万物繁富,始终向上、向前。一座城市使行者留恋,并不是缘于那些字面上的指标、数字、百分比。行行复行行,沙滩、大海、日出、日落、森林,还有漫长的海岸线,都是充满诗意的所在。正是它们,使短暂的数日生出此行不虚的美好。
《光明日报》(2024年10月11日 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