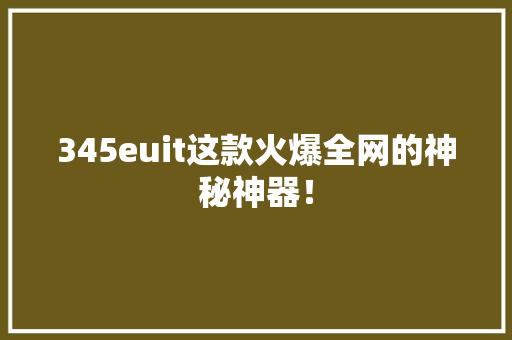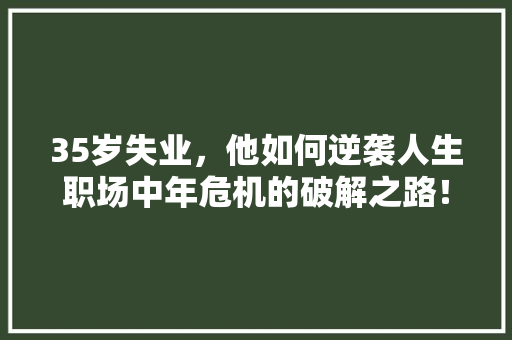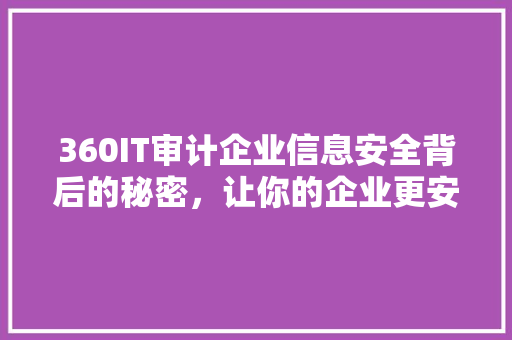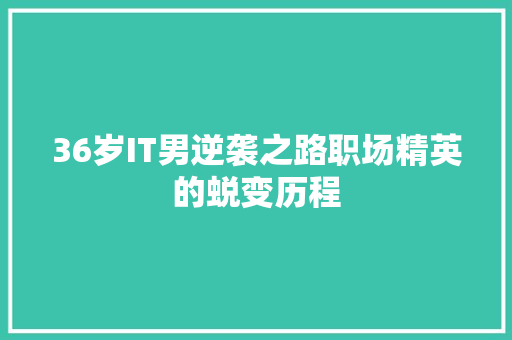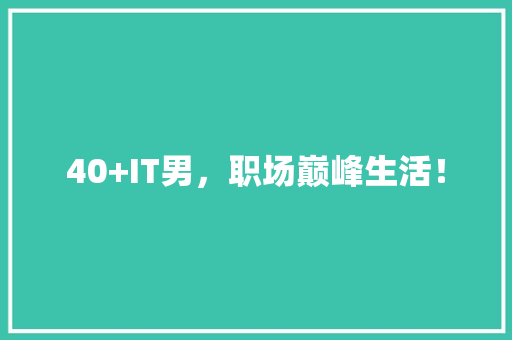择要:在北宋文人士大夫群体中,产生了对一种“精神愉悦”切实其实定、颂扬与造就,这种精神愉悦被命名为“清乐”。“清乐”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愉悦,是心灵不为物欲所累时的自由情绪,它是中国古代对美感或审美愉悦的称谓。得到清乐的紧张办法是从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进入大自然中,以林泉养心,以烟霞养气;也可以通过对艺术与文化产品的把玩与鉴赏而得到;清乐还来自心灵在自由中的升华,并产生一种“纯粹愉悦”。清乐是中国古代美学中审美愉悦的标识,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审美自觉—自律的标识。
有没有一个观点能够标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美感与审美愉悦?有,这便是清乐。“清乐”这一观点产生于北宋。大约从公元1060年到1100年40余年间,也便是从宋仁宗后期到宋哲宗在位的期间内,文人士大夫群体繁殖起了对一种“精神愉悦”切实其实定、颂扬与造就,这种精神愉悦被命名为“清乐”(也称“清欢”)。“清乐”一词所指称的那种审美愉悦,解释宋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正在进行一种非功利的、纯粹的审美活动,通过“清”与“乐”前所未有的结合,宋人将审美愉悦和其他可能包含有功利目的的“乐”明晰地区分开来。以当代之眼看来,“清乐”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愉悦,是一种“自由愉悦”,而“自由愉悦”是当代人所说的“美感”的核心。“清乐”的产生,意味着中国古人对付审美愉悦之特性的认识,从实践自觉走到了不雅观念自觉,并且将其确立为审美与艺术活动的目的。“清乐”的涌现因此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审美精神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并在之后的文化发展中扩大到审美文化的各个方面。“清乐”是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精神标识与精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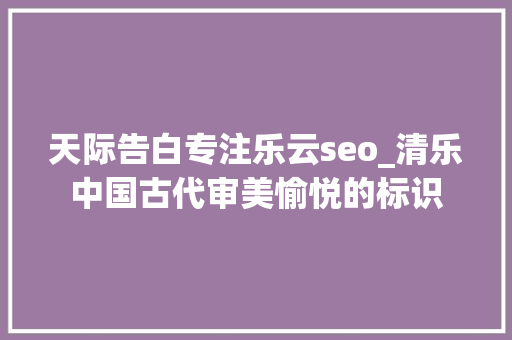
一、“清乐”的涌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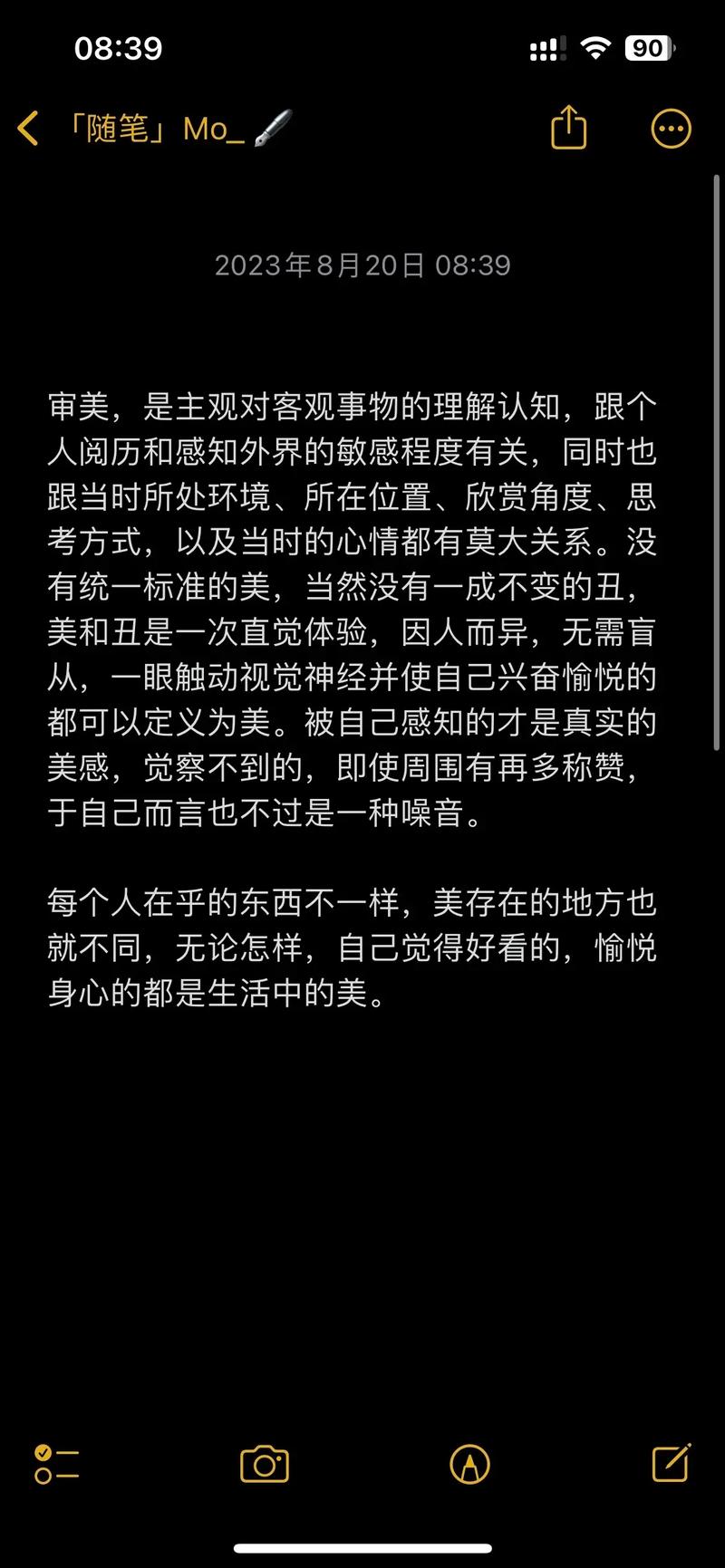
“清乐”以及它的同义词“清欢”,从仁哲期间宋人的语用来看,指一种愉悦,这种愉悦与欲念知足无关,与详细的功利性的知足无关,也与合目的性的道德愉悦无关。文人士大夫们意识到了有这样一种愉悦——这种愉悦是精神性的,也是自由的,这种愉悦可以来自对“自然”的欣赏,也可以来自对艺术的欣赏或某种文化活动,这种愉悦同时也是静不雅观性的。欧阳修较早地意识到了这种愉悦,他在嘉祐三年(1058)的一篇散文中,对人的愉悦作了一个两分——富贵者之乐和山林者之乐,他说:
夫穷天下之物无不得其欲者,富贵者之乐也。至于荫长松,藉丰草,听山溜之潺湲,饮石泉之滴沥,此山林者之乐也。而山林之士视天下之乐,不一动其心。或有欲于心,顾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获乐于斯。
物欲的知足会带来富贵者之“乐”,而通过欣赏山石林泉所得到的山林者之“乐”,可以得到精神上的知足——“自足而高世”,且这种“乐”“无累于心”,是一种与欲念知足无关的“静中之乐”。欧阳修没有为这种“乐”命名,但在“无欲”“山林”“无累”和“静”这些话语中,对这种“乐”的内涵进行了基本描述。稍晚一些,理学家邵雍在写于嘉祐六年的《名利吟》中,命名了这种“乐”——清欢:
名利到头非乐事,风波终久少安流。稍邻美誉无多取,才近清欢与剩求。美誉既多须有患,清欢虽剩且无忧。滔滔天下曾知否,覆辙相寻卒未休。
这段话区分了富贵者之乐——美誉,与山林者之乐——清欢。清欢显然是一种与功利性知足无关的愉悦。“清欢”这个观点的产生先于宋代,这一点稍后再述,但阐释“清欢”的非功利性和绝对性,却是邵雍的功劳,他倡导一种散逸、超脱、自由的心灵状态,并以此为乐。正如他不才面这首诗中所述:“清欢少有虚三日,剧饮未尝过五分。相见心中无别事,不评兴废只论文”。大约在邵雍阐释清欢的同时,宋代士大夫赵抃在《同周敦颐国博游马祖山》中说:“联镳归去尤清乐,数里松风耸骨毛。”赵抃所用的“清乐”,是现存文献中可看到的从“心灵之愉悦”的角度对这个词最早的利用。“清乐”本来是一个音乐观点,即清商乐,指称汉代至六朝时期的俗乐,沈括也说:“前世新声为‘清乐’(yuè),合胡部者为‘宴乐’”。但本文所引宋人诗文中的“清乐”(lè)显然是一个新词,“乐”不再指音乐,而是欢快喜悦。
“清欢”与“清乐”是同义词,总体来说“欢”比“乐”更强烈一些,清欢比清乐更感性一些,精神性更强一些,但究竟利用哪个词,或许是由高下文的平仄关系决定的。“清欢”一词,在唐以前的用例一见陶渊明,一见隋炀帝,但都不可靠,应出自五代或宋人伪作。陶渊明的用例见于署名后唐冯贽的《云仙散录》:“《渊明外传》曰:陶渊明得太守送酒,多以舂秫水杂投之,曰:‘少延清欢数日。’”隋炀帝的用例来自宋代刘斧《青琐高议》所载《海山记》,记中有炀帝《望江南》词八首,其七云:“湖上酒,终日助清欢。”这两例都不可信。这样,“清欢”这个词就找不到唐以前的可靠用例,最早看到是唐人的偶尔利用,到了宋代才成为一个常用词。有学者在《全唐诗》和《全唐五代词》正副编中各创造了2个用例,《全宋词》中则有41例,《全宋诗》电子版中可以检索到62例。
“清欢”真正广泛运用,要到宋仁宗、哲宗年间,个中最著名的,除了邵雍之外,应该是苏轼的名句:“人间有味是清欢”。黄庭坚也用过这个词:“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清乐”则以赵抃之诗为始被广泛利用。北宋黄履在《次韵和正仲游华严此君亭》中说:“吾曹对此但欲适清乐,不学渭川之人兮资千亩以敌万钟。”宋徽宗亦有诗云:“忘忧清乐在枰棋,仙子精功岁未笄。”“清乐”的利用在南宋更为普遍,如范成大诗云:“无端拙恙妨清乐,未许扁舟到五湖。”还有葛郯《柳梢青》词:“橘内仙翁,棋边公子,共成清乐。”
“清欢/清乐”的涌现与广泛利用,解释欧阳修所描述的那种山林者之乐,成为一种不雅观念上的自觉,为文人士大夫的心灵所喜,并且终极成为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对审美与艺术欣赏所得到的愉悦的代称。
二、清乐之“清”
“清乐”所标识的这种愉悦,之所以是审美愉悦,紧张由于它是一种非功利性的自由愉悦,而“非功利性”是通过清乐之“清”表示出来的。“清”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分外的意涵,它最初指水的澄澈宁静状态,而后类比为“气”之清浊和声音的宁静状态,并且在音乐中产生了由清商、清徵、清角构成的被称为“清乐”的曲调。终极“清”用来描述心灵不为外物所扰、不为欲念所扰的澄澈宁静状态,常日可组成“清虚”“寂静”“清淡”“清旷”等词,用以标示心灵的宁静与无欲状态。“清”所标示的心灵的澄澈宁静状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还被提升到存在论、人生不雅观和政治不雅观的高度。
“清”所标示的这种状态,在道家哲学中被上升到形而上的“道”的存在状态,进而落实为人生不雅观。《道德经》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还有“躁胜寒,静胜热。寂静为天下正”。在这个命题中“清”是道的一定效用。《庄子》对这个思想的阐发是:“役夫(指老子——笔者注)曰:‘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
这两个命题把“清”玄学化,使其成为道的本然状态,又通过“无为”,使道之清成为“宁静”这一天地存在的本真状态,同时宁静又是心灵的应然状态。这就使得个体心灵的“宁”、个体行为上的“静”,与道的“清”成为一体,形成从大道到心灵的体系化的玄学。这套玄学的核心观点是“道”,但其目的却是为心灵的宁静找根据,为“无为”这一政治空想找根据。在“与道为一”的宗旨引领下,道的寂静状态就哀求个体心灵也达到这种寂静状态。《庄子》对此进行了引申:“贤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男子,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
贤人之心静乎!
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从“天地之静”到“心静”,构成了人的心灵状态的指引。那么心灵的寂静状态又意味着什么?“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贤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者备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心静”意味着人生的无为,以及由无为而来的养生效果。但在道德实践中,“清”的心灵状态,引出了两种人格空想,一种是无欲则刚的明净、清直人格,如伯夷叔齐等隐世之士,孔子所称道的不肯与崔杼同流的陈文子,以及孔子本人的状态:“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另一种则因此清闲为务的散淡轻逸的自由人格,如《庄子·刻意》所述:“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空隙者之所好也。”这两种人格空想,总体上都是贞静自守与清心寡欲的心灵状态在道德上的表示,因此可以统摄为一种总体上的人格空想——超越于功名利禄之上的贞静与旷达的人格。
“清”这个词也指称一种情绪状态以及人生意见意义,喜好简朴而自然、节制而自由的生活。当心灵空灵,不被外物所扰之时,就自然而然地处于平和状态中,无缘而发,无缘而止,是其自由状态的自然呈现,总体基调倾向忧郁和惆怅,也会有愉悦、悲哀、无奈、幽怨、释然等。
凡是在心灵处于“清”这种状态时自然而然产生的情绪,大都可以和清再组合成一个偏正构造的词,如清悲、清怨、清愁、清欢、清伤、清悦,等等。这些情绪可以被称为“自由情绪”,或者说,是心灵处于自由游戏的状态时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情绪。这种情绪由于不是被外物所刺激,不是被功利性的知足或不满所引领,它是自由的情绪、非功利性的情绪。同时,这种情绪的“非功利性”还表示在,它不是由直接的生活所引发,而是在分开现实生活——或者说,在现实生活中断的韶光与地方发生,比如在进入自然之中并欣赏自然之美时,在从事艺术创作时,在欣赏艺术,操琴、焚喷鼻香、把玩古董之时,在书房中、在山间别墅中、在林泉之侧的草亭中、在所有那些由于生存而烦恼的生活情绪中断的地方,这种由“清”所标示的情绪才发生。这构成了此种情绪的另一层面的非功利性:它并不是由现实生活中的欲念与诸多情境所引发的情绪,而是在审美与艺术欣赏中,在一些特定的文化活动中自然而然产生的情绪。引发这种情绪的行为,都会受到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钟爱。如王安石在《太湖恬亭》一诗中说:“清游始觉心无累,静处谁知世有机”,清游这个词意味着,当一次游以清乐为目的时,它便是清游。以此类推,清玩、清谈、清鉴、清供等行为,由于以清乐为目的,都成为非功利性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总体来说,非功利性的自由情绪,是“清”一词的根本内涵,其他层次的内涵都是在这一根本上生发出来的。
“清”作为心灵的澄澈宁静状态,还会产生一种认知效果,这种状态在道家哲学中的另一种表达是“虚一而静”,在心灵的虚静之中,在涤除中,可以达到“心斋”“坐忘”的凝神虚怀状态,而在这种状态中又可以做到“朝彻和见独”,从而“同于大通”“与道为一”。这在荀子看来,是一种心灵的大清明状态: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心未尝不减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
后来阮籍在《清思赋》中给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阐释:“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飖恍忽,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皦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在心灵的寂静中,会产生神物来集、洞幽贯冥和泰志适情的效果,这便是阮籍所说的“清思”。这种具有创造性、洞察力并带来精神愉悦清思,构成了“清”这个不雅观念的认识论意义。
“清”所标示的心灵的澄澈宁静状态,以及它所包含的以上诸种意味,对付古代中国人的诗与审美,有深远的影响,并且成为诗学与美学的常用范畴。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以下几层内涵:清的基本内涵是明晰省净;第二是超脱尘俗而不委琐;第三是新颖和清新;第四是事物所引发的凄冽之感;第五是“古雅”。这个概括充分解释了“清”这样一种心灵状态在诗和艺术中的表现。但“清”的更高的美学意义还在于,它被提升为艺术的目的与艺术美的实质。《庄子·天运》篇引黄帝奏《咸池》之乐云: “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这里的“太清”,是“乐”的目的,也是“乐”的本源。这一点在明代的《溪山琴况》中有一个更明晰的剖析:“故清者,大雅之原来,而为声音之主宰。地不僻则不清,琴不实则不清,弦不洁则不清,心不静则不清,气不肃则不清,皆清之至要者也,而指上之清尤为最。”“清”在这里即是精神的本原状态,也是音乐艺术的目的和音乐美的实质。
在“清”的上述内涵中,产生了中国古代文化特殊是审美文化对付“清”这样一种天地状态与心灵状态的崇敬与追寻,而“清乐/清欢”的产生,与这种崇敬与追寻有一定的联系,这种一定性在于,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乐”。
三、清乐之“乐”
清乐之所以是审美愉悦,紧张在于它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愉悦,这种精神愉悦在中国文化中有其久远的历史渊源。《诗经》的《卫风·考槃》描述了一种隐逸之士的独乐状态:“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诗经》最初的阐释者们将“考”释为“成”,而将“槃”释为“乐”,从而让这首诗成为隐逸生活中精神愉悦状态的颂歌。在老子的思想中,强调一种“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的态度,超然于世俗的功名利禄之外,这种态度本身标示着一种心灵的愉悦状态。这都肯定了在中国古人的精神生活中,有一种不受功利束缚的人的生存的自由状态和这一自由状态所带来的非功利性的精神愉悦。在之后的历史演进中,这种非功利的精神愉悦得到了壮大与发展。到仁哲期间,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中至少还有三种愉悦可以被归为非功利性的精神愉悦:第一是孔颜之乐;第二是舞雩之乐;第三是不雅观化之乐。
孔颜之乐源于孔门弟子颜回在安贫乐道的生活中所表示出的精神状态——“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贫寒的生活中颜回的精神却处在一种愉悦之中,这是为什么?颜子所乐何事?这构成了宋明理学最主要的课题之一。周敦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敷,无不敷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周氏认为“乐”是由于心泰(见其大、见其道而心安),而心泰也是宋明理学阐释孔颜之乐的核心。之后的宋明理学关于孔颜之乐的阐释大概可以整理出这样一个线条:乐的出发点是“道”,孔颜之乐,是在“乐道”的根本上“安仁与安贫”,在安仁与安贫的根本上心泰,在心泰的根本上达到心诚,在心诚的根本上能“循理”,通过循理而达到与万物一体,顺生随性,在这个状态中得到心灵的愉悦。这种愉悦具有一种非功利性,或者说,它不是来自功利性的知足,而是来自心灵沉浸于精神天下时的得意与自乐,实在质在于:“与天道合一便可体会到内心的安乐,‘无事’、无惑、无忧、无惧,可以得到一个和谐的生存环境,从而感想熏染到物‘得其所’的天地大乐。”心泰的另一层意义在于,由于心诚与心泰,因此可以实现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即便有事,也不被事所扰。这种由诚与泰决定的泰然任之的心灵状态,以及物各得其所的和谐感与自由感,成为孔颜之乐的本源。但这种“乐”虽然可以纳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非功利的一壁,但显然是通过合目的性的认识与行为所得到的愉悦,它还不足自由,更侧重一种道德愉悦。
舞雩之乐源于《论语·前辈》中所说“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曾点给出的他的民气抱负,而孔役夫非常认同——吾与点也!
在舞雩之中有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愉悦,可以理解为一种“诗意生存”,因此自由与充足的面貌展现出的人的生存。朱熹对曾点的舞雩之乐作过如下阐明:“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盛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高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
朱熹的阐释从“人欲尽处,天理盛行”入手,肯定了其非功利性,又从“从容”和“乐其日用之常”中肯定了这是一种不离日常的精神愉悦;末了说“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高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肯定了这种“乐”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状态。按朱熹的阐释,舞雩之乐实质上是一种非功利、无目的、有形上代价的精神性的愉悦,这种愉悦在宋代士人阶层被普遍接管——“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舞雩之乐,可以说是宋代士夫阶层的精神寄托。
第三种乐是不雅观化之乐,是道家思想所倡导的一种精神愉悦。“道”处在生生化化的过程中,直不雅观这种生化过程,会得到精神愉悦;自然也处在这种生化过程中,对自然之生化的直不雅观也可以得到愉悦。在不雅观化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心灵上与道为一,与自然为一的状态,可以让心灵处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中。道家哲学,特殊是庄子学说,很在意这种愉悦。《庄子·至乐》有“且吾与子不雅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
”通过不雅观化与入化,庄子乃至可以超越死活之情。无论是濠上不雅观鱼,还是庄生梦蝶,还是藐姑射之神,在“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的齐物精神之中,贯彻着这种不雅观化、入化之乐。这种不雅观化之乐,小可以在不雅观鱼、草等微物中得到,大可以在不雅观山、不雅观海中得到,还可以在不雅观历史之兴衰中得到。这种不雅观化之乐,一贯是古代士人精神愉悦的一部分。唐代陈子昂的《登泽州城北楼宴》云:“平生倦游者,不雅观化久无穷”,而李白也有诗云:“探元入窅默,不雅观化游无垠。”这种愉悦在北宋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中更为普遍,如程颢《秋日偶成》云:“万物静不雅观皆得意,四季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这三种愉悦虽然都是非功利性的愉悦,但它们是不是“清乐”?——有联系与相通处,但清乐还有分外之处。与孔颜之乐比,清乐和孔颜之乐有同样的非功利性与精神性,但差异在于,孔颜之乐侧重道德愉悦,它所带来的愉悦与求道的执着与武断有关,与内心中的守一、执着有关,孔颜之乐中包含着庄敬之情,有目的,而清乐是无目的性的自由愉悦。
舞雩之乐中所表示出的身心状态,彷佛是清乐想要达到的效果,而舞雩之乐比较于清乐,虽然同样强调心灵的自由状态,但是舞雩之乐被授予了更代价化的内涵。它与“胸次”有关,与孔子所说的“志”有关:“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点知之,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使万物遂其性”,这意味着舞雩与万物存在的合目的性有关,通过感悟到万物的合目的性而得到的,也与个体精神的空想有关。而清乐更侧重自由,更轻松一些,是通过参与外物的“玩”而得到的,与合目的性无关,与空想的实现无关,它是通过“游”“戏”“玩”而得到的愉悦,它缺少舞雩之乐的庄严感,但更多自由感,因此清乐才更靠近当代人所说的“审美愉悦”。
不雅观化之乐最靠近清乐,但清乐不仅仅不雅观化,还不雅观“物”之清闲、得意,清乐比较于不雅观化之乐,多一些超然之乐。而且,不雅观化之乐将愉悦的源头紧缩在对自然之“化”的不雅观,这实际上缩小了愉悦的范畴。而清乐的来源,除在自然中不雅观化、不雅观清闲之外,比不雅观化之乐更靠近于书法、绘画、琴棋等本日所说的“艺术”带给我们的愉悦。“清乐”可以涵盖“不雅观化之乐”,以是清乐比不雅观化之乐更宽泛,在这个意义上也更自由。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清乐与这三种“乐”有交叠的部分,但作为一种精神愉悦,清乐比孔颜之乐自由,它不受道德的合目的性判断;清乐比舞雩之乐自由,由于它是无目的性的;清乐比不雅观化之乐更宽泛,由于它的范围比不雅观化之乐广。综上,清乐作为一种精神愉悦,是非功利性的,是无目的性的,是纯粹的自由愉悦。
四、清乐的精神内涵
对付一位仁哲期间的宋代文人士大夫而言,须要一个什么样的精神过程才能得到清乐?
第一,游于物外,从功利心、从物我之间的营役关系中解脱出来,或者说,采纳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来看待生活。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首先是指上文所引邵雍的《名利吟》所表达的从名利中解脱出来的态度。这种态度指向一种低层次的精神诉求——无忧。邵氏的说法在其后学南宋的熊节那里有过一个更明晰的表达,他注释邵氏“才近清欢与剩求”时说:“才有清乐处,分外求之。”注其“清欢虽剩且无忧”句曰:“清乐之多且是无忧。”把隽誉、美誉和清欢/清乐(熊节直接把清欢等同于清乐,解释清欢与清乐在宋代是同义词)对举,这里更多的是对付名利可能带来的祸事的恐怖,考虑到宋代激烈的党争和变幻的政治形势,这种避祸的心态大概是“清乐”之以是被重视的基本的社会性动因,但超脱名利之外是怎么实现的?苏轼给出了“超然”二字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即超然于“物”的差异之外,以一种“齐物”的精神来看待平凡之物与平凡生活,进而从美恶大小贵贱等区分中解脱出来。他在《超然台记》中说:“凡物皆有可不雅观。苟有可不雅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糟
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那么如何达到超然?苏轼的办法是“游于物之内”:“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不雅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不雅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因此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通过游于物之内,达到不争不斗的状态,从而享受日常的平淡生活,并知足于这种生活,从功利心中解脱出来,这就可以得到心灵之“乐”。
苏轼没有命名这种“乐”,也没有更进一步剖析这种“乐”的内涵。而在他写这篇文章大致相同的期间(约1073年,宋神宗熙宁六年),司马光在《独乐园记》中对这种“乐”进行了更精神化的解读。他写道:“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祍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相羊,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线人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
司马光描述的这种踽踽洋洋之乐,与苏轼所强调的非功利性的生活态度比较,更强调一种唯意所适、行无所牵、止无所柅的超然状态。这是一种心灵与个人生存的自由而独立的状态,虽然苏轼和司马光都没有用“清乐”这个词,但这种状态,是清乐的本源,是得到清乐的精神条件。
第二,当精神从功利生活中解脱出来之后,它会去做什么?——静不雅观万物。从一种非功利性的、自然的精神状态下来不雅观看万物,会看到什么?会看到万物清闲、得意与自由,用宋代理学家的话说,叫“万物之买卖”。这句话源自理学家程颢对“仁”的讲授:“万物之买卖最可不雅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直不雅观任何一个生命体,在之中感想熏染它的“买卖”,这是一个“体仁”的过程;而在得其买卖之后,会产生心灵的愉悦,这个过程和当代人所说的“审美”是相似的过程:通过感性直不雅观而得到精神愉悦。“不雅观买卖”由是成为仁哲期间文人士大夫在欣赏某物时的主导不雅观念,这哀求一种非功利性的直不雅观,而直不雅观的工具是“物”所表示出的在精神与生命状态上的“买卖”,由此产生对工具之惠爱——仁爱之情。虽然“物之买卖”并非“物之美”,但“不雅观买卖”确实构成了中国古人审美的一个维度,《二程集》中还记载了理学家周敦颐的一则辞吐:
周茂叔窗前草不撤除,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样平常。”
“自家”什么意思?——应该是自我感想熏染到的“买卖”。而这个买卖是可以放大的,成为“不雅观天地生物气候”。从不雅观“微物”之买卖,到不雅观天地生物之气候,这在超然物外、随意所适的心灵自由之外,得到了感知工具的非功利化的办法——不雅观物之买卖,在物之得意、清闲与自由之中,得到得意之乐——万物静不雅观皆得意,而这种得意之乐,实质上以“体仁”或者“不雅观仁”为目的,是对“仁”这种心灵状态的滋养,也因此仁爱之心、惠爱之眼,不雅观看万物之存在,从而产生心灵的愉悦。这种不雅观买卖之后的得意之乐,在明代王阳明的一首诗中得到了更明晰的表达:“闲不雅观物态皆买卖,静悟天机入窅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鸟自流形。”不雅观买卖,悟天机,在“自流形”的自由中得到愉悦,这是一种融惠爱与自由为一体的愉悦,这构成了清乐的第二重含义,这也是清乐不同于西方所说的“自由愉悦”的地方。不雅观万物买卖是得到清乐的第二步。
第三,在前两步的根本上,以自由与惠爱之心不雅观物,寓意于物,让物成为心灵与情绪的表现,成为意义的寄托与情之所寄,从而得到愉悦——这是得到清乐的第三步。直不雅观万物之买卖当然可以得到愉悦,但心灵面对万物时不是纯挚的直不雅观,它会选择,也会进行表现——选择“精神”与“意思”,表现“志”与“情”。
在关涉到心灵的自由愉悦时,仁哲期间的文人提出一个新不雅观念——寓物之乐:“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神于物。”留神于物,意味着对物充满功利性的诉求,心中有事,进而从事功的角度关注物的实存,“起计度之心”,这样就会“病于物”,因此宋儒认为空想的不雅观物状态,应该是“心不可有一事”。在这种状态下,外物和心灵之间是自由的关系,不被功利性束缚,这是欣赏一物的条件,在这一条件下,直不雅观工具时能得到什么?——物之精神。
邵雍谈到赏花之乐时说,“人不善赏花,只爱花之貌。人或善赏花,只爱花之妙。花貌在颜色,颜色人可效。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花之“精神”才是真正的审美工具,而欣赏物之精神,就须要“以物不雅观物”,即对物本身进行非功利性的直不雅观。“能以物不雅观物”,则“其间情累都忘去尔”,这种忘的状态,也便是心不为事所累的状态,是得物之精神的条件。能得物之精神,则“物”就可以成为心灵互换的工具,成为心灵的寄托,从而使寓意于物成为可能,这就为诗与艺术的创作供应了可能:
诚为能以物不雅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其或经道之余,因闲不雅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
在物我两不相伤中,因闲不雅观时,因静照物,在闲静中,心灵“乐与万物同其荣”,并借诗与艺术而得到抒发,这可以阐明为什么对诗与艺术的创作和欣赏是清乐的紧张来源。同时,在得物之精神之后,就可以感知到物之“意思”,即物在精神上的独特性,这来自苏轼在《真切记》一文中的不雅观念——“得其意思所在而已”。
得精神与意思并不是目的,终极的目的是“寓意”,是心灵中的“志”与“情”借寓物而得以抒发,并以此来寓欣赏者的情与志,而在寓意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乐”:“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丽人不敷以为病”。“言志”是中国古代审美与艺术不雅观念的传统,而言志必须通过寓物完成,而要寓意于物而不留神于物,则须要心灵的超然与惠爱。这让艺术欣赏成为得到清乐的一个主要方面——“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敷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
寓意于物,赏物之精神与意思,抒胸中情志,玩赏与创作字画,这构成了仁哲期间文人士大夫们寻求心灵愉悦——清乐——的日常办法。虽微物,可以娱心,在心灵的非功利状态下,万物的精神与意思都会显现出来,都可以成为心灵之寓,这也构成了宋人对待外部天下的“审美态度”。这种不雅观精神、不雅观意思,寓心于物,得乐于艺的过程,构成了得到清乐的第三步。
第四,在日常生活寓意于物的状态之外,得到清乐最紧张的办法是从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进入大自然中,进行自然审美,以林泉养心,以烟霞养气,从而得到清乐。
在自然山水中得到清乐,这在仁哲期间有普遍的共鸣,它的源头或许在于庄子思想和魏晋时的玄言诗中。在《庄子·刻意》中有一种闲旷无为的隐逸的生活状态(见本文第二节所引),但庄子并没有说这是一种“乐”。之后在两晋期间,这种乐得到了肯定,如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这天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不雅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以是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自然带给人视听之娱,这是一种“乐”。在谢灵运的诗文中,也可以看到自然给心灵带来的愉悦得到了某种肯定:“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栖之意得。……谢平生于知游,栖清旷于山川。……飞渐榭于中沚,打水月之欢娱。……山中兮清寂,群纷兮自绝。周听兮匪多,得理兮俱悦。”自然有其神丽,通过栖于山林之中,得清旷、清寂、清畅的内心状态,从而“得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悦?谢氏没有深述,但就这种悦的来源,他说:“灵域久韬隐,如与心赏交。合欢不容言,摘芳弄寒条。”这解释他认为在自然山林与人的心灵之间,会产生一种难以言传的“赏交”与“合欢”,这是于山川处得心灵之悦的缘故原由。
王羲之、谢灵运的这种愉悦在仁哲期间的欧阳修那里得到了回应,除了上文所说的“山林之乐”外,他还说:“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后得焉。”在自然山水中是可以得到至乐的,对付这种放心于物外、投身于自然的山林之乐,仁哲期间的画家郭熙给出了一个传诸后世的命名——“林泉高致”:
君子之以是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邱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
自然是人所常处、常乐、常适与常亲之所在,在自然中可以摆脱尘嚣缰锁,得到哪怕短暂的自由,这构成了欣赏自然的动因。而对这种山林之乐的神往,就构成了林泉之志、之心,也是林泉高致之所在,也因此能产生山林之乐:
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线人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践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斯岂烦懑人意,实获我心哉!
此世之以是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
这段话是描述山水画给人的愉悦的,但这种愉悦实际上是山林之乐通过山水画间接传达的结果,是山林之乐之以是发生的缘故原由。林泉之心是非功利性的,不留神于物的“自由之心”,它也是不雅观物之买卖、之精神、之意思的惠爱之心在自然山水中的展现,这种山林之乐,是一种“高致”,是超越性的,是自由的,也是精神性的,更是一种肉身存在的自由状态——仁哲期间的名臣富弼有诗云:“风雨坐生无妄疾,林泉归作自由身。”林泉和自由身之间,在宋人看来有一定的联系,这样一来,林泉就既是自由心,又是自由身,此二者共同构成了林泉高致的内涵。这种林泉高致,旋即在之后的中国文化史中,成为“山水”的精神内涵,成为山水画、山水诗所要表现的目的,从而成为中国文人艺术在敦仁、宣教、歌功、颂德之外最为主要的主题,它是清乐最紧张的来源,也是得到清乐的第四步。
第五,清乐还来自心灵在自由中的升华,并在升华中产生一种“纯粹愉悦”。这个征象最集中的表示是苏轼在《赤壁赋》中所记的心灵体验: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苏轼在自然审美中,得到了一种羽化登仙般的自由感,飘飘若仙,遗世独立。这显然不同于山林之乐,山林之乐更像是一种从人生羁绊中解脱出来后所得到的释然,而苏轼彷佛得到了一种更自由、更纯粹的愉悦。这种愉悦是怎么得到的?苏子有这样一段议论: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这解释,苏轼的愉悦源自处于自由与独立中的主体,创造了一个本真而澄明的天下,并对其采纳一种非功利的态度,这时月白风清可随取随用,自由无碍。苏轼的这种愉悦体验,达到了一种“同天”的境界,超越于在道德、认知与释然中所得到的愉悦,成为庄子所说的“逍遥”,这也构成了清乐的最高状态:一种无功利性、无观点性、无目的的、普遍的精神愉悦。
这样,得到清乐的过程也正是清乐的精神内涵逐步显现的过程,在每一步都可以得到清乐,但几种清乐间存在一个递进的关系。从最初的超然,到末了精神的自由状态,不同层次的清乐,表示着心灵不断趋于自由的过程。
五、清乐与审美愉悦
得到清乐的过程和当代意义上的“审美”是相通的,由于清乐与今人所说的“审美愉悦”是相通的,因而可以说清乐是中国古代人用来标示美感或审美愉悦的词语。如上所述,清乐是一种自由愉悦,而自由愉悦是自18世纪中期在西方涌现的当代美学所确立起来的美感或审美愉悦的实质,因此,从当代美学的角度来说,清乐所标示的那种精神愉悦,便是审美愉悦。
自由愉悦实际上是一种普遍履历,如没有含义的线条、一段好听的旋律、一幅没故意义的装饰画等,它们不虞味着什么,但能令人欢畅,给人愉悦。这个征象在18世纪得到了理论上的关注,比较于建立在认知和道德判断根本上的审都雅,这种愉悦更为自由,由于它不受合目的性的约束,不受观点的约束。这种自由愉悦和18世纪初期人们在道德领域创造的“非功利性”不雅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不雅观念:在鉴赏领域中,存在着一种与欲念知足无关、与道德不雅观念无关、与功利目的之实现无关的“非功利性的自由愉悦”,这种愉悦源于诸种精神能力,特殊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戏,源于人类心灵中的自由感,也可能来自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想象力之间的和谐感。这种不雅观念是18世纪美学的最主要的创造,并在康德美学中得到系统化的表述。
这个不雅观念可以阐释一些日常审美履历,比如天边流过的一片白云,溪边的一丛青草,一段无标题音乐,一行流畅的草书,山崖上一棵清闲成长的松树……这些东西都可以给我们愉悦感,而这种愉悦非功利,无目的,不含认知,无需比德,这些都可以印证自由愉悦的存在。自由愉悦在18世纪后期以来的美学中被寄予厚望,它成为审美自律性的基石,同时,自由愉悦作为美感,可以被自然、艺术与社会存在所引发,也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中被引发。因而自由愉悦可以渗透到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从而使得生活被审美化,也便是说,任何一个事物,只要能够引发我们的自由愉悦,就可被视为包含着美感。
从自由愉悦的内涵与表现形式来看,它和中国古人所说的“清乐”是相通的,如果我们把自由愉悦定为审美活动的标志,那么当然可以推论:清乐是中国古人的审美活动的标志。但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清乐”与西方人所说的“自由愉悦”比较,还有民族性与文化性的差异。
从非功利性、非观点的角度来说,二者是相通的,二者都是主体的心灵自由与工具的自由状态之共鸣的结果,但是二者仍旧有方向上的差异:自由愉悦侧重心灵的自由状态,特殊是想象力和诸种精神能力的自由游戏,得到自由愉悦的办法紧张是静照(contemplation);清乐则更侧重心灵的不为外物所扰、不为欲念所扰的澄澈宁静状态,在这个状态中,心灵由于独立而自由,但自由并不是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静”。可以作这样一个大略的区分:自由愉悦侧重自由感,而清乐侧重心灵的宁静感。从得到自由愉悦的办法来说,西方美学所强调的紧张是静照,这是一种直不雅观与反思相结合的状态,在西方人看来,只有视觉与听觉可以参与到静照之中。但清乐的得到,除了“静照”之外,还可以通过“清玩”、“把玩”(如文玩、字画、玉器、古董等)、“品鉴”(如品茶、品喷鼻香,乃至品尝山野味道等)某些工具的办法得到。
这种差异意味着,“清乐”可以涵盖西方人所说的“自由愉悦”,清乐中包含着以自由愉悦为核心的审美愉悦,因而得到清乐的过程是审美性的。但清乐中还包含着超出于自由愉悦的部分,这个超出的部分,便是中国古代人在审美上的分外性或者民族性。自由愉悦与清乐之间,相通处要远大于差异,即便在心灵的澄澈宁静状态这个最光鲜的差异处,也不能将二者断然区分开,由于在西方人的自由愉悦中,同样有从静照而来的心灵的宁静,因此,强调自由愉悦与清乐的同等之处而判断清乐是当代人所说的审美愉悦,这是可行的。但清乐的民族性仍旧应该强调,这种民族性是由清乐的得到办法与得到清乐的工具所决定的,也是由其精神内涵所决定的。
“审美”这个当代的西来术语所指称的那种人类活动,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所说的得到清乐的过程,是相通的。“审美”这个行为的标识是“非功利性的精神愉悦”,而“清乐”同样指称这样一种愉悦。在这个相通处,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追求清乐的活动标识为“审美的”。“清乐”一词所指称的这种精神愉悦,因此成为标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对付审美之独立性的不雅观念上的自觉—自律。
这种精神愉悦并不是在仁哲年间才有的,古代中国在魏晋期间就已经实现了审美自觉,有一些词汇,如“心远”“真意”“清音”等都含有“清乐”之义,而在王羲之、谢灵运等人对自然与艺术的欣赏中,非功利性的精神愉悦就已经成为他们审美愉悦的核心。但“清乐”这一不雅观念的涌现解释,宋人在不雅观念上认识到了这种愉悦是与人类的感官快适、肉身快乐、道德愉悦或认知愉悦不同的,并用“清乐”一词来标示审美活动的自律性。
自从清乐在仁哲年间成为不雅观念的自觉之后,南宋和明代的文人士大夫们普遍接管了这个不雅观念,并把自然审美、文艺鉴赏、古玩收藏、琴棋娱乐和休闲养生等活动中所得到的愉悦,统归为一类。如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的媒介中说:
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而风雨忧闷辄居三分之二。其间得闲者,才三之一分耳。况知之而能享用者,又百之一二。于百一之中,又多以声色为受用。殊不知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先生长西席,多畜法书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支配,篆喷鼻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不雅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娑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间。所谓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人鲜知之,良可悲也。
赵希鹄(1170—1242)是南宋人,他认识到在声色知足之外有一种愉悦,这种愉悦可以通过自然、文玩与艺术而得到,他没有用“清乐”一词,而是用了“清福”一词来命名这种愉悦状态;明代屠隆的《考槃余事》明确地认识到自然欣赏与文玩活动有一种“乐”,没有用“清乐”来命名,而用了“清赏”一词来解释这种“乐”的来源;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也没有利用“清乐”,而是侧重于物之“雅”,并相信赏物之“雅”可以有某种“乐”。以上三人所述,其精神旨趣,都可以用“清乐”来概括,也便是说,在清赏之中所获的清福,以及赏物之清雅所得到的乐,都是“清乐”。
在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中,特殊是《燕闲清赏笺》中,他对清赏所带来的乐,有了更系统的描述。在《燕闲清赏笺》的媒介中他说:“时乎坐陈钟鼎,几列琴书,帖拓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喷鼻香霭,栏槛花研,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而后在《燕闲清赏笺·论历代石本》中记其所见《开皇兰亭》的感想熏染云:“余向曾见《开皇兰亭》一拓,有周文矩画《肖翼赚兰亭图》卷,定武肥瘦二本,并禇河南《玉枕兰亭》四帖,宝玩终日,恍入兰亭社中,饮山阴流觞水,一洗半生俗肠,顿令心目豁达。”高濂所述这种通过清赏而得到的清心乐志、心目豁达状态,正是“清乐”的详细表现。
结语
在今人看来,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们在生活的诸多方面寻求清乐的过程,正是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过程,这是由于这些生活形态包含着可以用“清乐”来概括的精神愉悦,因而“清乐”一词可以作为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审美愉悦的标识,也是中国古代美学中可以用来标识审美自觉—自律的理论术语。只管实践中的审美自觉与自律远比“清乐”这一不雅观念产生得早,但“清乐”这一不雅观念的出身意味着,古人从不雅观念上确证了审美愉悦的独立性与审美活动的自觉—自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清乐是古代美学中审美愉悦的标识,也是古人所意识到的审美自律在不雅观念上的标识。
(本文注释内容略)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